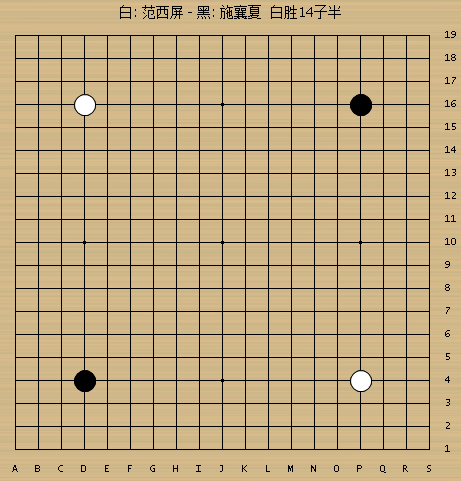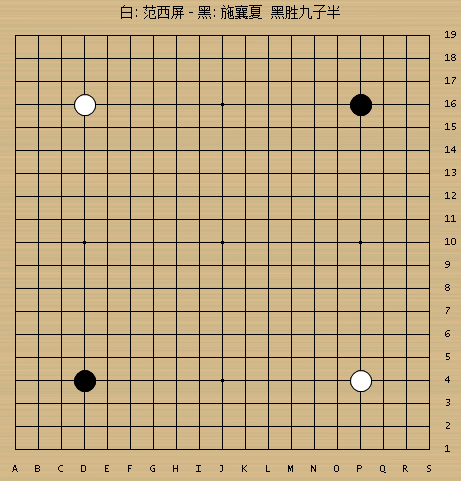【围棋小说】胜负手 – 7
(三十一)
入冬后,柳娘终于耗得油干灯灭,撒手人寰。柳莺哀痛葬母后只身一人来到吴令桥家。嫚屏既知是西屏所托,又见她也端的可怜,便嘱人安排她住下照顾大朵小朵的饮食起居。
柳莺多苦多累的活都做过,现在这点活就不觉得有什么苦了,抽空还学了些描画花样和刺绣,嫚屏也挺喜欢她。因绸庄兼做绣衣、绣袍、绣裤、绣鞋、绣褥、绣帐、绣椅搭、绣帘、绣幔等几十种绣品,又承揽了少量宫廷的衣物刺绣,包括官服的补子,官员流行的腰间佩饰品褡裢、荷包,不免要时常翻出些新的花样,柳莺有时别出心裁设计出的图案花纹也多被嫚屏采纳。
闲暇里,她悄悄给西屏绣了两个围棋盒的套子,请街上的篾匠用细竹片依尺寸编了一对盒笼,把绣了花的杭缎套子严严实实蒙上,十分玲珑别致。只等有机会就送给西屏,她相信爱下围棋的西屏一定会喜欢。
只有一件事让她十分忐忑不安,就是这家的主人吴令桥常借故和她亲近,让她躲不胜躲,防不胜防。母亲一生的教训告诉她不可轻信有钱的人。但对于吴令桥的所作所为,既不能张扬,又不能给他个下不来台。因为闹翻脸之后,她将如何自处?吴家呆不下去,她又能到哪里去呢?
谁知这样一来却让吴令桥觉得这女孩是欲迎还拒,骨子里却是个狐媚的精怪,越发对她心心念念不能释怀,在生意百忙之中也要偷出空来借故悄悄拿些唐诗宋词话本小说之类的书让她读,明里是要她长些识文断字的入门功夫,暗藏的心思却是若她有不懂之处不免有求于他,便无端多了些一近芳泽的机会。
这一番心思柳莺如何不明白,但只能以年纪尚幼作天真烂漫之态,含糊应对。那些书倒是对了口味,只管囫囵吞枣读了下去。有些故事原是母亲说给她听过,却不知其出处;有些律诗绝句幼时也曾记诵过,可是有些是只记了字音并不知道是什么字,意思也难以贯通。现在从书中发现了那些诗句,确有意外的惊喜。不少词句对于她未免过于艰深,但她抱定了主意,不懂的东西也不深究,存了心思待有机会再问西屏。吴令桥若耐不住拿出关心的架势问了起来,她只说字也认不全,哪里能读懂,还没有那些手抄的绣谱看得好玩呢。
说绣谱好玩也不全是推搪之语,范嫚屏托人辗转从松江民间绣坊抄来顾绣的工艺,光针法就有施、搂、抢、摘、铺、齐以及套针、刻鳞针等数十种,琢磨起来有无穷的意味。又有顾绣的绣品可供对照,用到后坊间的刺绣中产生的效果有时确实出人意表。柳莺每有心得就说给嫚屏听,嫚屏有时忙不开就让她先用简单的图案绣出效果再看。柳莺得了任务就潜心尝试各种针法,不知不觉成了绸庄各种新品研制的得力成员。嫚屏渐渐倚重于柳莺,有时连借得的唐宋名家字画要勾勒底稿,这样重要的工序也交由她来完成。柳莺索性建议专门请一个画师来教大朵小朵书法绘画基础,她也可在旁边附带增加些学识,以备日常之用。嫚屏一发依了她的话,果然延请了一位老画师,隔三岔五来绸庄教习。大朵小朵是娇惯出来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自由自在爱学就学,只当是个好玩的游戏,柳莺却是上了心的,那个认真劲连老画师也感到意外。因知柳莺在吴家不过是个婢女伴读的身份,见她如此专心有时到了贪痴之境,竟不知自己拿了薪酬到底是来教谁的了。
无论如何,自此柳莺的书画技能得以迅速提高。
吴令桥见柳莺一门心思全扑在辅助嫚屏琢磨刺绣的工艺上,全顾不上与他搭腔,有苦却也说不出口。他万万没料到这正是柳莺存心拟就的自保之计,只以为是自己的攻略出现了偏差,便改变了思路,以后但得了什么小巧稀罕之物,便瞅没人留意的时候送给柳莺。柳莺拒也拒不得,只索一派天真地收了,日积月累竟在屜角旮旯里堆作一堆。吴令桥什么场面没见过?欢场上的各色女子也见得多了,他从来没想到过,对付一个看起来还未谙世事且无依无靠的女孩子要费这么多心思。
(三十二)
转眼已是冬去春来,西屏师从山阴俞长侯学棋已有半年之久。同门师兄弟虽有七八人之多,但出类拔萃者还是施襄夏和范西屏二人。
西屏入师门虽晚,但进步神速,原与施襄夏有三子之距,近日同门师兄弟之间的交战,他们二人的棋力已在伯仲之间了。
令西屏难以忘怀的还是俞长侯先生给他上的第一堂课。
那时西屏因连日下赌棋,习惯于不假思索便落子如飞,自己的病处不补棋,只盯着别人的病处,结果与施襄夏的第一盘被授三子棋行至中盘,已成全盘崩溃之形。范西屏见俞长侯不动声色在一旁观战,窘得无地自容。
俞长侯止住二人行棋,借机对大家道:我对你们常说棋不可贪,贪则必为对方所乘,因为既言贪就肯定有当补不补之棋。我也对你们常说另一句话,叫棋不可不贪,意思是发现对方的破绽之处要大胆抓住不放,不能轻易放过。这两句话互为补充,即是行棋的常理。赌棋必贪,故我不准我的弟子在外面下赌棋。其实若是棋达到一定的境界,下赌棋原是无妨的。但是,谁能达到这个境界?
这境界就是物我两忘,循理而行!
俞长侯转身盯住西屏道:我知道你下赌棋有不得已的苦衷,规矩只自今日始。我这里还有个自定的规矩,只和弟子中的第一名下授子棋。希望你尽快提高棋艺,我等着和你对弈一局。但愿不会让我等到老眼昏花!
一番话说得西屏如醍醐灌顶。
他开始静下心来,全身心投入到棋艺的钻研中。他的基础和领悟力比较好,很快就超过了其他几位同门师兄弟,直追施襄夏。
但要超过施襄夏又谈何容易。施襄夏是所有师兄弟中最肯吃苦的一个,起床最早,睡觉最晚,只要有一丁点空,他就要盯在棋盘上,因此得了个外号叫苦行僧。连师兄弟们一起偶尔上一趟街市,他也不肯奉陪。
山阴地方并不大,青石板的道路贯穿整个街市。街边的茶舍酒肆各自打出自家的幌子,随风在行人的头顶上飘动,黄酒的香味随时随地直往鼻腔里钻。西屏只在过年时喝过一次黄酒,也就一小碗,原以为没什么力量,谁知这酒后劲绵长,一个时辰后他还晕头转向。
俞先生遂借题发挥道:有人下棋东一子西一子看似毫无章法,到中后盘时,这些散兵游勇似的子突然发力,一以当十,且力道绵绵不绝,一不留神就会优势逆转。这和黄酒有异曲同工之妙!
俞先生兴致高时也带弟子们一起爬周边的小山坡。西屏脚力强,总是冲在最前面爬到顶,俞先生最后登顶,喘息方定便道:作为一名棋手,登高才能望远,才能胸有全局。拘于一城一池得失的局部一役或可胜利,但离棋盘稍远一点你就会发现,大局不知何时已然落后!有这样的见识,才能成为高明的棋手。
这种妙譬随手拈来,不着痕迹,西屏在这种氛围下,对棋的理解日益加深。
西屏的战绩对施襄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为现在只有施襄夏才有和师傅下棋及当面聆教的机会,其他人只能在施襄夏手中打升降极,若西屏闯过了施襄夏这道关,对于施襄夏来说,这些得天独厚的机会就将失去了。所以在授先对弈阶段,两人拚得异常艰辛。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原先,施襄夏接到妹妹的来信,总要和西屏学说一番,因为施颜每信必问及范兄近况如何。西屏便嘱施襄夏复信时加上几句话,问候颜妹习学书画进展如何。到两人剑拔弩张为第一大弟子之衔而战时,这种轻松的交往已然断了档。
最后一次授先十番棋之战西屏以十战七胜艰难过关。它意味着施襄夏此后和西屏只能以分先对弈。
西屏因激动而夜不成眠,因为有了这战绩,俞先生已答应从明天起和他下授三子棋!
这个结果对施襄夏的震撼更为巨大,同样一夜无眠的他竟然出现了丝丝缕缕的白发!
(三十三)
施闻道因献计祭海弄潮会错上意被辞馆已达半年之久。对于从事幕业的师爷一行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幕中就业,时称就馆或就幕,寻求馆地叫做觅馆或谋馆。这一觅一谋二字,反映了这一行业维持生计的艰难。在幕业中,素有搁笔师爷之说,这意味着幕业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等待或曰寻觅就业的群体。事实上,几乎所有当师爷的都有过搁笔的经历,他们在不断更换馆地的过程中都曾或长或短充当过这一特殊群体的成员。所以施闻道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新的机会。
他的如夫人朱氏倒不担心施闻道搁笔在家,凭他的能耐找到新的就馆之所是迟早的事。她最关心的是两个孩子的前程。儿子去学围棋,原是不指望作正经事业的,好歹应该读书挣个出身才是。但浙江一省被停了乡试会试,又不知何时才能重开,儿子就算埋头读书又有何用?女儿一天一天长大了,上门求亲的也有不少起,但都被施闻道婉言拒绝了。常言说得好,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这是她最大的心病了。她为这件事跟施闻道说了多次,有差不多合适的就行了,也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光哼哼哈哈就是没个章程。
这天又来了个媒婆,是个见面熟的。朱氏数番周折让施闻道打了回票,情绪也就不再如当初那么高涨,只懒洋洋例行公事般地问些男家的来历什么的。媒婆一张口倒把朱氏吓了一跳,原来这一个还真有点来头。对方是巡抚朱大人家的三公子朱亦平。朱氏不敢怠慢,立马让人请施闻道出场。
原来那天西湖游园,朱亦平正在画舫里和一班朋友吟诗作对。他本是个多情的种子,酒意正酣中看到的施颜在湖畔垂柳之下,飘飘如仙,灵感受到激发,那天的即兴诗作妙譬连连,公推为最佳。事隔了多日才隐隐约约想起那个湖畔的女孩,且总也忘不了。辗转找那天一道游湖的朋友询问,总算有一个回忆起来说那个女孩是有点面熟,似乎是巡抚衙门中谁家的小姐。经过锲而不舍的追踪,最后打听实了是父亲的前任钱粮师爷施闻道的女公子。
朱亦平是朱拭夫妇最疼爱的小儿子,平日里就指月亮不能给星星,娇痴中自有一种蛮霸的脾性,他这么见风就是雨自说自话地看上了施闻道的女儿,这让朱拭十分为难。一来这门亲事显然门不当户不对;二来才辞了她老子的职,却又托人去说亲,于情于理上都说不过去,就不长不团地拖了下来。
谁知这三公子这回却真真切切无端害了单相思,茶饭不思不说,也不去外面跟那帮朋友瞎掺乎了,眼睁睁一天天瘦了下来,眼窝下陷,眼神呆滞,跟中了邪似的。再加上夫人的枕边风一阵紧似一阵,朱拭无奈何,只好纡尊降贵托媒人去说合。
施闻道一听是巡抚大人的三公子,却也惹动了一番心事。这朱亦平他是见过的,长相才情都不错,但这种公子哥你要指望他不在老子的庇荫下自己撑起门户做一番事业那是根本免谈。求亲的意思定是这三公子执意的结果,做老子的没有理由支持这门亲事,自己刚被辞馆,朱拭竟然能抹下这副面子向自己开口,可见这公子受宠到何等程度。
从施闻道的角度来看这门亲事,无疑是高攀了的。但以他长期从事幕业的精明,却知道是官三分险,保不齐哪天皇上听信了谁的一句挑唆,这乌纱帽就没了。当年范子豪因一盘棋怠慢了钦差丢了官就是个活生生在眼面前发生的例子。更惨的不仅仅是丢官,弄不好还得搭上脑袋,有的人甚至自己脑袋不保不说,还会有抄家灭门之虞。自雍正登基后追究拉亏空的官员,一二品的方面大员也不知倒了几多。其中有不少官员还确有冤情,因为细究这亏空拉下的原因,却正是前朝皇帝的南巡所经之处,地方官为巴结天颜而广修临时驻跸之行宫或游乐处所而致。雍正在宫中事必躬亲宵衣旰食,倒也没养成南游扰民的嗜好,否则杭州府的地方官要拉下亏空的第一个就是巡抚朱大人!
如此想想,却把高攀的想法丢到爪哇国去了。这边厢收住脚步也不去见媒婆,只差人递个话给朱氏,就说且容我们家里人先打个商量再回话。
(三十四)
施颜却完全不知道她的命运顷刻间在不同的指向上打了几个来回。
对于她来说,这世界依然充满了令人憧憬的未知的画面,而她所要做的仅仅是用一支画笔挥洒自如地去描绘。
尽管没有手把手示范,但方士庶的一番指点对她的启示非常大,因为方士庶的山水画受学于黄鼎,再上溯即是清初六家中的四王,他们在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深厚的功力,在笔墨、构图、气韵、意境等方面有独到之处,方士庶在前人基础上除特别强调笔墨工夫,追求苍秀灵动而外,又不排除师法自然,主张师古而不泥古,比之他的老师境界有新的拓展。他的这番见地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施颜,她把这种追求实施在山水画的创作中,果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能这般平心静气地专一攻画于她也属难得,这和哥哥不在家她极少有机会出门也不无关系。
说平心静气那也是作画时的状态,稍一闲暇,也会无端引得她浮想联翩。
虽然事隔很久,她还是能想起那天西屏在湖边看到她着裙装目瞪口呆的样子。每回想一次,她都要偷着乐好半天。又想到他在盐官镇要她让九子然后把她的棋冲得七零八落,那个得意劲,自然也要在心里暗发一回狠。联想到祭海弄潮那日被海潮呑没的一刹那,失魂落魄的味道,再加上衣冠冢落葬自己不争气眼泪不断,全让哥哥瞧了去,后来受了多少奚落!当然也要把账记在范西屏头上。就这么乐一回,恨一回,想一回,不知不觉,竟和援笔作画一样成了每日的功课。
有一天施颜忽起一念,要给西屏画一幅人物。她素来是想到就做,便收起正在画的一幅山水,另铺开纸即兴构思。她沉吟片刻,立即得了灵感,假托一少年牧童,在水牛背上光着屁股往溪水里扎猛子。如何命题是个关键,若是径题弄潮儿,虽则可收讽喻之效,一报让九子大败之仇,但毕竟失之直白。思来想去,却题作“可知深浅无”。这句话却是由唐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中借来。想那溪水若是浅的,这顽皮的牧童一猛子扎下爬起来必是一头污泥,那神态定将尴尬无比。为了表现水的深浅,她在不引人注意的画面一角上另添了只鹭鸶站在水中作悠闲状。
构思停当,画到半途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那牧童的脸自然要酷肖范西屏才是,可是到落笔时施颜才发现,她竟然无法描摹出他的面部形象!
整个人的形象是清晰的,但眉毛是宽是窄,眼睛是大是小,嘴唇是厚是薄,完全没有细部,可见自己从没有敢认真从画师的角度端详过西屏。
反过来一想,西屏对于她是不是也忆不起形象来呢?呀,不定他现在成天乐成什么样,把自己给忘干净了也说不准。
从哥哥的来信中,间或可得到西屏的一星半点情况,开始还提及得多些,包括俞先生敲打他的那些小故事。后来光说他长棋了,只能让他一先。再后来就绝口不提西屏什么事,似乎这个人已经从人间蒸发掉了。最近收到哥哥的来信突然又报说西屏棋力已和他旗鼓相当,难分高下,故现在他们俩都可以直接和俞长侯先生下授子棋。又说不久在杭州将有一场高手会战,俞先生准备带他们俩去观战。
想到不久又能见到西屏,施颜心里一阵乱跳。这么长时间没见,他是不是又长高大了?这次见到,他会不会还像上次那样犯傻气呢?
她坐在桌边,手轻托着下巴在那儿静静地想着,不觉已经痴了。
半晌,施颜才惊觉过来,回到眼前发生的难题,心里为自己转圜道: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想当然耳!
好在可将面部设计成多半个侧面,纵不逼真勉强也可以含混得过去。
她没有丝毫气馁,依然兴致勃勃完成了这幅作品。
至于如何把自己的这幅画送到西屏手里,她还没来得及想。
(三十五)
俞长侯近来面临无端的困扰。
原因是近来有几位外地棋手经过山阴,因知俞长侯的名头都以讨教之名前来挑战。俞长侯让他的两大高足联袂出场,结果剑锋指处所向披靡。既然弟子一关都过不去,那些外地棋手向俞长侯挑战的话当然再不会提起。
赢棋当然不是坏事,但俞长侯从两弟子和别人的对弈中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因为自从俞长侯宣布在他们俩没分出高下之前与两人都下授子棋之后,两人渐渐都接近了他的棋力,表现在战绩上就是从授三子,授二子,直到授先,二人的进阶之路几乎是寸步不离。但到此为止,再无明显长棋迹象。
面对外来棋手则不同,从他们的对局中可以发现求胜的渴望和对杀时的自信,比之同自己下棋时判若两人。疑问即由此而产生。
由于传统上师傅是永不与弟子下分先棋的,如果弟子棋力超过师傅,要么选择离开,要么选择代师授艺。而判断弟子的棋力是否超过师傅,必须由师傅自己提出郑重其事地下一次定胜负的授先番棋。弟子胜者出师,负者到时机成熟再以番棋定去留。如果师傅不提出考较弟子真实功力,弟子可能一直不逾雷池一步,永远不会胜过师傅。
俞长侯担心的是他们实际上已超过了自己的棋力而自己却并不知晓,从而耽误了他们棋艺提高的进程。
警觉之后,俞长侯打算在适当时机提出和他们俩分别下授先番棋,在此之前,他还想让那些比自己棋高一招的围棋大家来考较一下他们的真实棋力。他们没有师生之份,范西屏和施襄夏定会全力以赴展示他们的实力。
恰在此时,徐星友托人带信来,说有两个年轻的日本僧人来杭州永福寺修习佛法,二人均是高段位围棋手,数月之内对前往挑战的棋手未尝有过败绩,在杭州棋界引起轰动。为此邀他来杭州先打头一阵,并说已捎信给程兰如,也请他拨冗助阵。二阵他拿不下那两个日僧,只有请程兰如作最后一搏。
俞长侯欣然答应,请来人回话给徐星友,近日即动身来杭州府。
他决定带两位高徒同去,一来可以观战开阔眼界,二来有机会也可让他们一展身手。
西屏听说有机会出门已是喜出望外,又说是去杭州,恨不能蹦起来了。
能去看高手下棋,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因为这段时间除了和施襄夏对局是使出了全身之力,和其他师兄弟们下棋可以说无需太动脑筋,授子棋下多了,对上手棋的感觉必然迟钝。同时,这一段时间和俞先生之间的对弈也很别扭。因为他的棋路受先生影响较深,局部的走法本来有新的思路和试验的可能,在与先生对局时就不敢出手。尤其是传统定式的变招探讨,私底下和施襄夏对局时一旦发现可有不同的变化,即行大胆变招,不用担心先生的指斥。与先生下则只能一成不变地行棋。他发现施襄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自从俞先生破例答应与他们二人同时下授子棋后,施襄夏的情绪缓解了一些,与西屏之间也不似前一段时间那么剑拔弩张。两人之间的对局虽然不多,但复盘探讨棋理倒比以前更加频繁。在二人关系的缓和上,西屏倒是主动得多,但施襄夏看得出,西屏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有机会,他总是转弯抹角地想套出一点施颜的消息。三番五次之后,这个当哥哥的在这方面再不开窍也总算闹明白了,西屏是喜欢上了他的妹妹施颜!
有了这个发现,施襄夏算是掌握了一手秘密武器,叫西屏往东他不敢往西!作为补偿,时不时也有意无意地透露点妹妹的动态,看到西屏假作镇静地听着,其实瞎子都能感觉到他的急切和兴奋,施襄夏有一种恶作剧后的志满意得。
3,134 total views, 2 views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