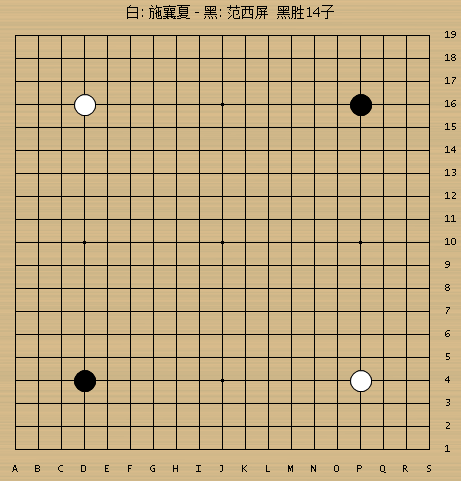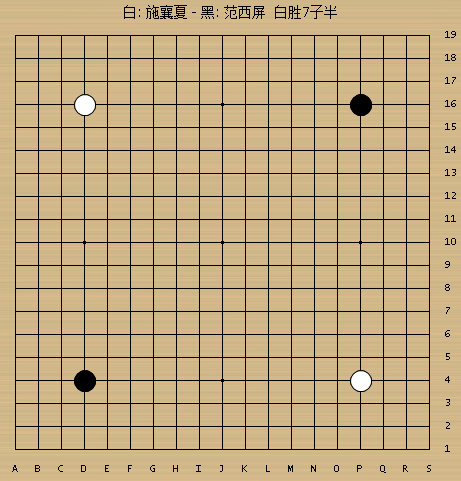【围棋小说】胜负手 – 6
(二十六)
徐星友与程兰如已在吴山一家茶楼上纹枰大战数日了。
吴山是西湖南山延伸的山脉,春秋时是吴国的南界,由紫阳、云居、金地、清平、玄莲、七宝、石佛、宝月、骆驼、蛾眉等十几个山头形成的弧形丘冈,总称吴山。杭州人俗称之为城隍山。这一带的茶楼比较多,但江湖汇观楼的名声比之其他茶楼又要高出一筹。但看大门上这副对联就不同一般: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
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
这是山阴人、青藤道人徐文长留下的墨宝。晚年他贫病交集时曾在这一带寓居,屡番自戕而未成,但留下的文字一百三十年后读来却依然气贯长虹。作为其乡党,俞长侯提议徐程之战在这里进行也是颇有一番深意的。
徐星友致仕后苦研棋艺,棋力大涨,但离一流水平还差得很远。因久闻国手黄龙士威名,不惜重金请至家中,因黄龙士比徐星友还要年轻几岁,恐其不耐与下手周旋,遂不惜密寻勾栏美色以诱之,且令其若即若离,使黄龙士留连徐舍,徐则潜心讨教棋理,后果有大成。最后两人下了十局授三子棋,其实这时黄龙士授三子力已有所不逮,但仍勉力为之,虽互有胜负,但对黄龙士来说堪称呕血之作,故后人称之为血泪篇,亦不为过。
对于徐星友来说,程兰如是后生之辈,他的棋风素以搏杀见长,对杀时算路精细,稍有破绽即如鹰隼般全力扑击,揪住不放,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和等闲人对弈难得下到收官子,往往棋至中盘即已了账。
俞长侯礼节性地向程兰如讨教了一局后,由徐星友和他分先连战数局,皆尽败北。吴令桥不时来照上一面,打个哈哈,安排下酒食便即忙他的事体去了。汪一凡和宁儿已回扬州,但郑克柔和方士庶二人还愿盘桓几日,正好前不久有人拜托吴令桥找书画名家指点一二,他这个顺水人情也可以还得不费周章。郑方二人便在西湖周边和吴山一带优哉游哉玩得个不亦乐乎。
这一天下午,吴令桥带了他的那位朋友来见郑方二位。给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巡抚朱大人府上的师爷,施闻道,我的朋友。
施闻道因祭海弄潮的主意出砸了刚让朱大人给辞退回家,此时却不便说,只在鼻腔中打个混便让随他同来的施襄夏和施颜向二位执师长之礼。郑克柔马虎道:不用多礼。你们俩都学书画?
施闻道笑道:这个是哥哥施襄夏,书画只略知皮毛,平素爱棋,已随山阴俞长侯先生学了半年围棋。这个是他的小妹施颜,为出门方便着的男装,她学了几年书画。
吴令桥道:巧了,俞长侯正在这楼上观战呢。
施襄夏闻言立即上楼去拜见师傅去了。施颜展开自己的几幅字画习作请两位老师指点。郑克柔见是几幅山水,便道:方兄长于山水画,你先评说吧。我忘了徐文长那个“火”字那两点是如何写的,再到门口看看去。
方士庶素知郑克柔是散淡之人,只索由他去了,随手拿起施颜的一幅山水品鉴。因见她的画作虽然技法生涩但不乏灵气,当得个清新有趣的断语,只得点评道:画因流派不同而风格迥异,不可一概而论的。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景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衡是非,定工拙矣。我自己立意追求的是笔墨苍秀灵动,尤其强调笔墨工夫和趣味,若能以笔墨的精妙,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那就是上上之境了。我观此画已初窥门径,但临画作画莫如师法自然会来得更加真趣盎然。又说了一些亲近山水的必要。一番话听得施闻道都连称谨受教,施颜更觉这寥寥数语却如拨云雾,心中实感到获益良多,便大着胆子向方士庶请教一些技法掌握和意境营造方面的问题。
下午,徐星友与程兰如的一局棋已有胜机,但在一个局部之争中徐星友陷入长考。施家父子和俞长侯在一旁观战。茶楼的伙计闲话说隔壁那间屋里这几天有个十几岁孩子天天在那儿下赌棋,棋很厉害,彩金也重,今天已经又赢了几个大人了。
说者无意,听者留心,俞长侯闻言悄悄踱了过去。
(二十七)
只见这边屋里几桌棋都闲着,唯有靠窗一桌围满了人。下棋的孩子有十四五岁模样,精瘦有神,但眼睛发红,口唇起泡,看起来十分疲惫。俞长侯问了对局彩金,竟是一局一两银子!再问那闲话的伙计,这孩子白天黑夜几乎全在这儿不走,似无家可归的模样。已赢了不少银两但也不怎么花销,只索一碗面一个烧饼,就是一顿,像是急等钱用的样子。有个棋客输了棋欺他人小耍赖不给钱,他几乎跟人家拚命。那个人愣是没赖过去,闹得好生没趣!
再看他的棋,别人只要一落子,他不假思索随手即应。思路之清晰,反应之敏捷,却也罕见。俞长侯看他的对手投子起身,一时心动坐在了他的对面。
俞长侯沉静地问:你急等着要用钱?
那孩子一愣:是的,先生。
多少?你这样下棋会累垮掉的。
二十两。不,越多越好。
欠人家的?
是的,我欠人家一条命。
俞长侯看他说的很认真,不像开玩笑,就接着说:你的棋不错,可是这样的下法,你的棋就毁了,知道么?
我们下一盘吧,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先生。
俞长侯掏出一两银子递给那孩子:算我输了一盘。
那孩子咬了咬嘴唇,唇边的水泡破了,一丝血迹慢慢渗开来:你想和我说什么?
你不是本地人?
是的,我是海宁人。
你不说我也听出来你是海宁人。俞长侯笑了,叫伙计过来,吩咐了几句话,伙计点点头出去了。围观的棋客们不明所以,都在窃窃私语。
俞长侯道:我就请个海宁的棋手来和你下一棋。
施襄夏和施颜说话间走了进来,俞长侯道:我来给你们介绍——
施颜已经惊叫起来:是你!你,你,你怎么还活着!
范西屏也站了起来:原来是你们!
这下轮到俞长侯惊奇了:你们全都认识?
施襄夏道:这位叫范西屏,我曾和他下过棋。就便简要把范西屏应征当弄潮儿被大潮卷走的事向俞长侯讲述了一遍。
俞长侯想起来了:郭唐镇先生向我荐过你,他在你家,不,在你二叔家当过多年的私塾先生。后来有你父亲的消息么?
西屏摇了摇头。到这时他才知道郭先生叫郭唐镇。
范西屏不愿再提父亲的话题,遂对施颜道:我那天一直在水里挣扎,到杭州才让人给救上来,谢谢你给我送葬。说到这里他才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
施颜想起那天下葬时情形,忽地红了脸。见西屏嘴角上有血丝,从衣袖中拿出了一方锦帕递给他,示意他擦擦嘴角。
施襄夏这才又插上说话:这位是我的老师俞先生。弟子愚钝,若说这半年我在围棋上水平略有寸进,全是老师悉心指导的结果。
范西屏瞬间想到自己和施襄夏是被授三子的水平,他的老师水平至少又得高出一大截,而自己刚才差点跟他叫板下分先棋!想至此已是额头见汗,万分不自在起来。捏在手中的锦帕也忘了擦嘴角,只无意识地在额头上擦了几下。
俞长侯见他面露惭色,暗起怜才之意,遂道:你想不想和施襄夏做个师兄弟?
施颜见范西屏还愣着不说话,忙点醒他:俞先生要收你为徒,傻样!
范西屏略显诧异地瞅了施颜一眼正色道:西屏不是不明白,只是尚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未了,哪里也去不得。
(二十八)
柳娘的咳喘之症是日甚一日了,咳久了便咳出血痰来。看了许多次,郎中也没什么好方子,只是不断换些汤药煎服,总也不见好。柳莺近年来常帮着在水边浣洗衣物,还要不时寻郎中替母亲诊治,心中茹苦却无处诉说,每日里强作欢颜忙忙碌碌。这日正在江边累得筋疲力尽时,猛一抬头,范西屏却意外地站在旁边。她一声未出,却止不住把眼泪抛撒了一串,在水中激起一路小小的涟漪。
哽咽了一会才挤出一句:不是叫你不要来我们这种人家么!
西屏笑道:真不来怕要给你骂死啦!
知道会骂你什么吗?
那还不清楚?忘恩负义啦,狗眼看人低啦,过河拆桥啦。
柳莺道:心里也许会这么想,我才骂不出来呢。
这才破啼为笑,让西屏帮着她把洗得的什物拎回去。西屏拎得也感到吃力,暗忖柳莺那细弱的身体也不知平日是怎么对付下来的。
到了家门前,吴令桥已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
吴令桥是稍晚一些知道西屏的事情的,送走了郑克柔和方士庶,便随西屏一起来柳家。因柳家所居住的是贫民聚居的处所,担心西屏年轻不懂事白给人骗去了银两。到了柳家只有柳娘一个人病势沉重在屋里躺着,阴湿的屋里弥漫着一股中药味。西屏按柳娘说的方向去江边寻柳莺,吴令桥耐不住屋里的气味,就在屋外向周围随处看看,边看边摇头。
好不容易远远见西屏和另外一个女孩出现,吴令桥心下已打定主意让西屏给她们家一笔钱两清不欠,省得日后被缠住脱不了身。
两人走到近前,吴令桥见柳莺年方十五六岁,虽是家常衣饰,但也难掩其天然丽质,只觉得她相貌秀美,清纯可人,心里暗称真瞧不出这西屏人小鬼大,难怪这么用心。
当下西屏把赌棋所得的银两全部留给了柳莺,让她再请郎中为母亲诊治。
柳莺见这么多银两,吓住了:你,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可不能去做坏事呀!
西屏笑道:你揣摩我去做飞贼是么?我这是正经挣来的。
吴令桥解释道:这小子在茶楼整下了几天的赌棋,差点累得爬不起来。要不是我一个朋友撞到他,现在他还在那儿玩命呢。其实他根本用不着那么玩命,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
西屏接口道:反正现在我这命也是白拣的,没见人家都给我下了葬了么。
柳莺再三推拒不掉,只得收下了那些银两。
一时想起来又问:赌棋要遇上比你厉害的人怎么办?
西屏道:厉害的人多,没给我碰上。就碰上一个还成了我师傅。又把要跟俞长侯先生去山阴学围棋的事说了。
在避开柳娘后柳莺悄悄说:郎中说娘的病是没有法子治的了。说着又掉了阵子泪。
吴令桥心思瞬间已转了十八道弯,见状大包大揽道:不要伤心了,大夫治病不治命,若万一真治不了,这姑娘以后就留在我们家照顾小女,这么点年纪一个人在这里也不成个事。
西屏没想到吴令桥如此爽快,忙一揖到地代柳莺谢了。
吴令桥对柳莺道:谁让你们母女救了我们三弟呢,这也是我和他大姐该做的事。西屏这下就可以放心地跟俞老师到山阴学围棋了。
柳莺只剩抽泣的份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范西屏究竟还是孩子心性,想到自己可以静下心来和这样高水平的老师学习棋艺,心中也是一阵畅快。
告辞柳家母女后,在路上吴令桥问西屏:这家的男人呢?
西屏便约略把那个负心的扬州商人的事说了一遍。吴令桥再问那个商人的姓名,西屏却不知道,只说十六年前是常来杭州的,突然一下就没了踪影。
吴令桥心里格登了一下,口中却道:以后可以托扬州的朋友找找看。难道这人他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想?真够荒唐的!
(二十九)
柳娘的病势愈加沉重了,眼窝深深陷了下去。
柳娘自知时日已不多,这天经前思后虑,终于叫住了忙前忙后的女儿。柳莺见母亲的神色凝重,知道有要事交待,便倚在床边候着。
柳娘缓缓言道:莺儿,一直以来我没有和你说过你的父亲的名字。
柳莺道:我不想知道。
柳娘喘了几口气方道:他对不起的是我,但他不知道有你这个女儿,你不要记恨他。他其实也不是一直没来过杭州,我在杭州就亲眼见过他一次。
柳莺惊道: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不可能,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认识他。不过他的身边还有个女人,年轻漂亮,十多年他的变化也不大,有钱人活得滋润哪。
你没有和他说话?
我当他已经死了,怎么会去和他说话。再说,我是他什么人哪,就说出来也没人会相信。男人就是这样,好起来把你比作天上的月亮,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来巴结;一旦有了新欢,马上把你给忘到九霄云外。
怎么当初就看不透他呢。
哪里是看不透,只是一心要逃出那种风花雪月的地方,慌不择路了而已。柳娘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当年的场景,嘴角挂上了一丝笑容。
他那段时间天天找一班朋友去吃花酒,专门给我捧场,花钱跟流水似的。年轻和美貌真是好呵,不管说什么人家都用笑脸对着你,你只管撒娇,只管发脾气,人家也不知道生气,反倒一个劲地罚自己喝酒。唉,那时候我也是太年轻,不知道男人都会朝秦暮楚的,总以为自己侥幸碰上一个会巴心巴肝跟你好一辈子的人。他给我赎了身后,我是满心满脑都是他,再忙再累也不怕,就怕他有一点点不高兴。但是,那一段的好日子像梦一样,还是说没就没了。
柳娘的叹息声尚在胸腔中酝酿,来不及通过口唇便淹没在一阵窒息般的咳喘中。
半晌她才续道:那一次他又跟一班生意上的朋友去喝花酒,回来醉得不省人事。我好意劝他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谁知他借酒装疯,说那些地方怎么啦,那些地方不去怎么会碰上你这种尤物!把我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就三天两头找茬子闹别扭,似乎怎么看也不顺他的眼了。
他是盐商,做的生意很大,但也常常有不顺意的地方。有一次他为生意的事要去求盐政官员,带我去应酬场面。那官员喝了酒言语和动作都十分不堪,他见了像没事人似的,我难以忍受便借故逃了席,那天回来后他跟我大发雷霆。我被激怒得失去了理智,一个人跑到钱塘江边准备跳江了结生命。他寻到江边,苦苦相劝,又指天赌咒发誓,才劝得我回去。
就这么好一天歹一天的,但那时候已经有了种种不祥的征兆,直到有一天真的他突然消失,无非是应验了这个征兆而已。
难道这世上就没有真情实意的男人?
太少了,莺儿,真的很难碰得到。
那,像范公子这样的人也会朝秦暮楚吗?柳莺觉得难以想像。
他完全可以不再来我们这里,可他还是来了。
他还小,人是会变的,有时候可能会变成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柳娘说着一阵急咳,几乎要昏厥过去。柳莺忙着给母亲捶背揉胸。柳娘好一阵折腾从喉间挤出一口血痰,这才缓过劲儿。
过了良久,柳莺还是忍不住问:你说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三十)
西屏这两天总算是见识了做大生意人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吴令桥家所开的天龙绸庄在杭州的绸庄中不算太招眼,一般的也是前店后坊。东园巷一带织机声整日里不绝于耳,织出的绸缎都要在几家绸庄的柜台上出售。
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以来,杭州从商人数增多,说杭民半多商贾,也没大差。丝绸业是其中主要的产业之一,其所产绸缎营销各地,还出口东亚国家及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吴令桥接下乃父的生意后即改做出口,近几年兼做宫廷生意,比起别家绸庄来格外显得要生意兴隆。由于杭州这一带地方的丝质好,所织绫绸轻盈柔软,细腻而有光泽,花纹清晰,所以宫廷里的大量袍服都是采用杭绫杭绸作面料,用暗花织物作袍服衬里。这对多家绸庄来说,都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夺的绝大买卖,稍不留神就会别人截走,托关系找门子的开销不说, 这种生意头绪多事体杂,整日价几乎就不着家,静下心一想却似乎什么事也没做,无非是忙于上下打点,迎来送往,尽是场面上的应酬。
大姐范嫚屏擅刺绣,兼顾花纹图案的设计,还要和丝行打交道。因为绸庄的原料要靠丝行和蚕农交易代购,设若不了解丝行的门径,平白无故就会遭受损失。一般丝行都靠那些有丰富经验的掌柜,收丝时眼、手、心三到,通过观察和手的触觉去估算捆扎物重量,唱价秤码,使卖户口服心服;秤好付款以后,就请买户挑选。挑中的买去.对帐结算,细心的还要剪除附着物,再秤一遍净丝,来日上税后,再让送往其绸庄。这种交易俗称“抄庄”,即代客买卖。绸庄本是有专门的人来料理这种生意的,但嫚屏总是不太放心,有大宗的生意更要亲力亲为,故平日事情也多得难有闲暇,尤其是四月小满过后,农人忙于换选剥茧,缫丝出卖,接上五月旺季,肩挑背担的蚕农成群结队而来,春蚕丝量多,继以夏蚕丝,一直持续到七月。忙起来也就照管不了两个双胞胎女儿大朵小朵。入秋后稍闲些,故见吴令桥领了西屏来,还可以问长问短说说闲话。听说了西屏的一番离奇境遇不免感慨万千,又以大姐的身份加以叮嘱,并亲自安排好他的吃住,让他宽心在家里呆几天。
西屏却是住不惯,见大家都忙于生意,一个人呆着真是百般无聊。明天就要启程去山阴了,施襄夏说下午要陪范西屏逛一逛西湖。西屏经历这一段正感到身心俱疲,能这样放松心情自然是求之不得。早早便从大姐家出来,一个人寻到断桥边,等着施襄夏。
虽然听过大姐描述西湖的景致,毕竟百闻不如一见,不知不沉中西屏随游人步上断桥,但见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市,湖光山色相映,端的如诗如画;再细瞧那水面上鳞波跳跃,堤上柳丝婆娑起舞,轻舟画舫浆声欸乃,恍惚身在仙境,不由记起幼时读过苏轼的那首绝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一头沉吟一头却是低诵出声。
正在神游物外的遐想中,肩膀上被人轻拍了一下。转身一看,却是一个不相识的女孩,笑嘻嘻地望着他。说不相识,面庞眉眼间却又那么熟悉,似曾在那里见过。
你认识我?西屏迟疑地发问,无来由地心通通直跳。
女孩点点头,轻启樱唇一本正经道:适才正在湖底小憩,听先生在此屡唤西子,西子便来了。
西屏呆住了。西子?眼前这一位,白皙中略有些羞红的脸庞,漾着盈盈的笑意。细看瓜子脸上那一对滴溜溜转乌黑的大眼睛,眼神既透着得意,又有些怨怒,像是在责怪自己如此愚钝。这一切都那么眼熟,只是头上泛着淡绿色莹光的珠钗和自然垂落的长发让西屏发怔。女孩着一条淡绿色绉纱裙,一根粉红色丝带随意地拦腰束住,亭亭玉立在湖边,微风吹过,柳条、长发和纱裙都随风飘动。
西屏如入梦境,连忙拍拍脑袋又揉揉眼睛,却见施襄夏立在一旁微笑着瞧着他。
那女孩突然格格笑起来。
西屏猛然省悟:你是施颜!怎么你是女的?
施襄夏道:小妹施颜,她是我的跟屁虫,非要跟来不可,我就是拿她没办法。
施颜学西屏刚才的傻样,又是拍脑袋又是揉眼睛,越发笑个不了。西屏好生尴尬,佯作生气不准施颜再学,三人便说说笑笑沿湖慢慢走去。
施颜记起那天赌棋的事,因问道:那个救了你性命的母女俩怎么样了?
西屏摇头道:她母亲的病很难治了,只拖得一日算一日。
那女孩以后怎么办呢?
我大姐答应收留她照看他们的孩子。
施颜便定定地想事儿,不再说话。
施襄夏和范西屏转而说了些跟俞长侯学棋的一些讲究,又说到那天隔壁下棋的是国手程兰如和徐星友,徐星友连输了几局老面子差不多都丢尽了,好不容易那天占了上风,是赢定的棋了,可程兰如苦思冥想却走出一个四劫连环,愣走了个和棋出来,把徐老先生气得胡子直翘!范西屏听了不免啧啧连声。
许久插不上嘴的施颜突然盯着西屏来了一句不相干的话:那个女孩,她长得漂亮么?
3,198 total views, 6 views today